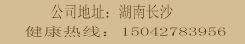展厅墙面上有许多不同几何形状的小框,大多成组、紧密地排列,也有个别离散在群组之外。深浅交替,让人想到打开的书页。蓝色、米色或黑白,这些小框在墙面上堆叠成颜色与建筑组群,把墙面变得如纸薄;又像一面面小窗,将当前的空间与另一端相接。
AsthaButail,Turningtowardspurewhite,
这些抽象的墙面装置来自印度艺术家阿莎·布塔尔(AsthaButail)长久以来对口诵传统(OralTradition)的浓厚兴趣与田野调研。年初,在印度班加罗尔SKE画廊举行的个展“存在的轨迹”(LocusofBeing)展出了八件与《梨俱吠陀》(RigVeda)和印度当地的口诵传统相关的作品,运用了木、铜、乐器、棉线和手纺平织布等多种媒材。布塔尔认为她的作品“占据而非构建空间”,且“空间是由观者对存在的意识所决定的。”
AsthaButail,LocusofBeing个展作品,
节奏是布塔尔试图通过作品重现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具体触感。《不动之动》(ImmobileMobile,)中,60个小框以不同的速度与频率运动,营造出节拍器般重复的节奏;《日将出》(Thesunwillrise,)中,31个小框以太阳出落的节奏定义昼,每个框代表一昼,共同形成对一个月的定义。这些小框的尺寸好像是精密绘图的产物,似乎遵循着某种隐性的秩序感。布塔尔还会令人惊讶地运用“无声”让我们领受这些节奏所天然带有的声音。如《部分真空》(PartialVacuum,)通过改造笛、鼓、簧风琴等乐器的发声装置使其“失声”,以此探讨听觉的“真空”,从而喻示一种失传的语言,并延展到失传的文化。在梵语表演《静之誓》(Vowofsilence,)中,因发誓沉默而禁止自己发声的布塔尔用玻璃笔书写无形的回答。
在这场展览中,唯一透露了口诵传统所依赖的作为介质的人的作品,是《十个方向》(10directions,-)。观者可以打开10个非对称的抽屉,其中藏有25张诗意的字条,分别体现出同情、爱、自由、平静、痛苦、憎恨、失败、挫败、悲伤等情感。这些看似恒常的人类情感,经历了漫长的人类文明进化史,与理性相纠缠,在口诵传统中被保留下来。布塔尔的最新作品几乎是《十个方向》的续作,这件名为《(3+1)柜子》((3+1)CABINETS)的装置以三根铜管连接四个柜子和一张含有四个凳子的长凳。“我希望为每一种文化都构建一个共享的、可相互参照的基础。……长凳象征人性,三根铜管寓意三种并行的口诵文化——波斯、犹太与印度吠陀。”观者可以开关抽屉与滑门,发现内部的一些物件或字条。这些物件和字条,都与布塔尔最近的一次长途旅程相关。年,布塔尔凭借其提案“当书写缺席时”(IntheAbsenceofWriting)荣获最新一届宝马艺术之旅,从年6月到年3月,如愿以偿地探访了三大口诵文化,实地走访了伊朗亚兹德,以色列耶路撒冷,英国伦敦,印度的瓦拉纳西和新德里,拜访当地的口诵技巧教学作坊。
AsthaButail,CrossingⅤ,
每到一地,布塔尔都会邀请受访者进入一个特制的帐篷进行访谈。帐篷作为一个相对私密的会客空间,并不向公众开放,而仅限受邀的亲身实践口诵传统的学者或学生。帐篷的设计会随地点的不同而改变,比如采用不同密度的手工平织布作为帐篷的面料,而平织布也是布塔尔创作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材料。通过帐篷,她将这些实地调研的现场转化成了一种属于她的创作空间。
要了解口诵,首先要意识到记诵依赖语音。在印度,吠陀唱诗所用的语言是吠陀梵语,而其字母来自源于婆罗门文字的梵文字母,其辅音与元音的发音会根据其在单词中的位置而变化,这被称作“字母的花环”(var?amālā)。在伊朗,阿维斯陀语(Avestan)的字母被称为DinDabrieh或DinDabiri,在中世纪波斯语中意为“信仰的手卷”。“信仰”(Religion)一词的拉丁语词根是“Religare”,意为“自我重复”。而在耶路撒冷,希伯来语在复兴后成为了一门活的语言。这些语言都在各自的传统中被用来保留原本的口诵信息。
AsthaButail,IntheabsenceofWriting,
口诵是一种仅凭口口相传、而不借助文字的传统。在印度,诵诗依赖一套严密的记号系统,运用严谨的数学序列与图案来帮助记忆。有时会刻意用倒序来记忆。这些规范与技巧都让口诵更像是一种机械式的复述,其意义被刻意地同语音分割开来,让人的背诵与语音成为历史的单纯媒介。布塔尔说:“口诵记忆应当是群组式的。……口诵传统是一种与相应文化紧密贴合的表演和能量。”
口诵用的吠陀梵语与古梵语不同,但唱诵基本上用的都还是吠陀梵语。布塔尔介绍说在希伯来语中也有类似现象。圣经中的希伯来语和今天常用的希伯来语也不同,不过主要表现在书写上,口语发音还是基本保持一致的。这也是让口诵传统能够延续的一大原因。
为了调研,布塔尔需要克服巨大的语言障碍。在大多数会面中,都是她、受访者与翻译三人同时在场。在旅程开始前,布塔尔就已经学习了梵语。她告诉我,梵语不能算是自然形成的语言,它不是从市井中诞生的,而是由精英为了学术与宗教而构建起来的人造语种。“当然你也可以说所有语种都是人造的,但梵语是一种对自我角色认知非常清晰的语言,它的构建即是为了传达最崇高的精神与智识之美,几乎触碰到了人类智力创造的极限。它同时还拥有一种超凡的微妙。”
AsthaButail,IntheabsenceofWriting,
梵语属于印欧语系,对构建古印度文明至关重要。公元前年之前的思想记述用的基本都是梵语。梵语的词形变位非常丰富,比如从名词的结尾可以判断其数量(单、双或更多)。再如,从一个词就能判断其在语句中的位置,因为作为主语和宾语的词的末尾各不相同。如果想表达的意思是“和它一起”、“为了它”、“来自它”、“在它上面”或“属于它”,这个“它”的末尾都不一样。因为一个词需要有表达单、双及更多三种数量状态,因而仅一个名词的词形变位就多达24种。在此基础上,可能还有其他28种根据时态或其他语态而导致的不同变位。也就是说,总共有28乘24种不同组合来表达一个名词。动词的变位就更多了,有上百种,非常复杂。公元前四世纪的印度语法学家帕妮妮将梵语语法简化到了条语法规则,所以只要掌握了这条语法规则,你就能搞定梵语了。
AsthaButail
我请布塔尔分享一首她学梵语时的古诗,她就先向我科普了《梨俱吠陀》诗集。这部诗集分为10组曼陀罗。因为口诵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书,所以没有目录,而每一圈曼陀罗代表了一组目录,读者可以从每一圈中选择起始点,从而构成许多不同的组合(有点类似中国的回文诗)。布塔尔选择了No5.82(这个编号代表的是5号曼陀罗中第82号诗),她说更理想的情况是录一段语音,但因为种种原因,还是暂且先用文字表述:
TatSaviturVrinimaheVayamDevasyaShreshtamSarvadhatamTuramBhagasyaDhimahi
(那愉悦,那满足,那最佳的或那最强大的成就,那能承载万物的胸怀,那极乐的主宰,它达成了目标,而我们选择它将我们自己包裹)
AsyaHiSwashstaramSaviturahkachchanPriyamNaMinantiSwarajyam
(他的自我胜利存于他的欣悦,比任何人更甚,他是这欣悦的主宰,这欣悦无人能将它破损分毫)
QA
Q:您作品中的秩序感让我印象深刻。对您来说,秩序感意味着什么?
A:作品中的秩序感对我来说十分重要,我在秩序感中找到平静。在我的作品中,每个单元都像一段编码,一个实体,并且总是相互关联,好像彼此之间可以对话,亦无法孤立存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形成了一些数学模式,并代表着生长。而生长离不开秩序感。
Q:请问出行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有发生什么意外吗?
A:虽然我在出行前做了许多调研,仔细列了一个拜会访谈的名单,但总会有原本没在名单上、但很重要的人冒出来,让我惊喜不已。
Q:这次旅行对您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A:至年,我把一种名为金哈(KINKHAB)的古老镀金布料用作《幸福七轭》(SevenYokingsoftheFelicity,-)的材料。在瓦拉纳西,只有两家工厂能将金做成金纺线。这组蓬帐形的装置展示了布与线之间的转换。通常,金哈只能用24英寸的小型织布机织造,但我特意设计制造了一款36英寸的织布机来实现这件作品的尺幅。
AsthaButail,Sevenyokingsofthefelicity,-
对我来说,金象征着口诵传统的延续。而这次旅程让我在创作中纳入了不少新材料,诸如铜、水、空气、空间。同时,我也将创作拓展至表演与录像等非常强大的创作媒介领域。虽然归功于技术进步,如今大量的口诵祷文已经被写下来了,但这也会伴随着一种取代或削弱口诵传统的风险。与此同时,文字记录却也在保护口诵内容免于流失。但其实表演和影音的记录形式比文字更重要,因为它们可以把语音也记录下来。这也将是我在创作中会继续尝试的方向。
Q:金、木、水、火,这些基本元素或者说能量经常出现在您的创作中。在您看来,这些元素在口诵传统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A:我很认同你的观察。木、火以及刚才提到的金,比较容易让我们想到能量。但是,在不同的口诵系统中,对水的祷文相较其他元素而言,才是最特别的。在印度,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习水祷文。每餐前都要唱诵水祷文,小啜一口水后才能开始用餐。在一些特殊场合,水祷礼会有特别的仪式:在一张铺满稻米的床上,水被盛在铜器中。通过集体或重复唱诵,能量被注入水中,而经唱诵的水就被认为是吉利的。家人会将其洒满房间各处,以消除空间中的负能量。在伊朗,如果祷告用的水不是井水或井干涸了,那相应的仪式都要暂停。在耶路撒冷,水祷意味着净化。在这次的新作品《(3+1)柜子》中,水流经铜管,一如水与水祷文连接万物。
AsthaButail,BroadenedSky,
Q:在您看来,语言的变化对口诵传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A:口诵史可以追溯到年前,而语言的演变不断受到新时代的影响,书面语受到的影响相较口语还来得更多。可能唯一保持不变的是大部分语音。有趣的是,我在两个相隔遥远的地方接触到了非常近似的语音,一个是印度南部的廓尔喀语,另一个是亚美尼亚犹太教徒的语音,两者基本都用喉部发音。
Q:对您来说,之于历史,书写与口诵有何不同之处?
A:年,理查德·贡布里希(RichardGombrich)在牛津大学的首场讲座上提到,现存的梵文手稿共有万卷,而古希腊与拉丁文手稿合起来才3万册。相形之下,留存下来的梵文书卷是海量的,其中不少手抄本仍保存在私人图书馆与寺庙中。这些文集体量之庞大超乎想象,内容从各种性交体位的绘本、算术、吊大象的指导手册到建筑、天文、医学、宗教、语法、地理等等,包罗万象。如果我们要去比较口诵史与书写史,那么口诵需要做到一字不漏,所有内容必须熟记于心。所以口诵史是一种复述,而非讲故事,它不会根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演绎。也就是说,口诵是没有作者的。
文/顾灵
*本文原载于周末画报
本文由赫兹文艺独家发布
未经许可请勿复制转载
如果你也有一颗文艺的初心
想要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