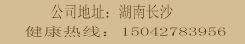![]() 当前位置: 乌贼 > 乌贼的形状 > 教师节特辑父亲的求学之路
当前位置: 乌贼 > 乌贼的形状 > 教师节特辑父亲的求学之路

![]() 当前位置: 乌贼 > 乌贼的形状 > 教师节特辑父亲的求学之路
当前位置: 乌贼 > 乌贼的形状 > 教师节特辑父亲的求学之路
父亲的求学之路
——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父亲和他伟大的老师们
(一)颠沛流离的小学
父亲出生于年2月,在那个局势连年动荡的年代,我们大苗庄大多数时间属于唐河县源潭区白鹤里乡管辖。爷爷弟兄三人,父亲是他这一辈人中的老大。当时一大家子在一起生活,最多的时候有15口人,有四五十亩地,爷爷是这一大家子主事的。和旧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一样,如果风调雨顺,日子勉强过的下去,如果遇到天灾,就只能听天由命。
年秋,父亲被爷爷送到我们村西南2里地的常庄小学校,走出了艰辛求学生涯的第一步。那时,爷爷目睹了好多农民因为不识字而经受的种种艰辛和厄运,决心再困难也要供应父亲读书。并且,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个家族的老大往往被寄予更多的希冀与担当。
在简陋的常庄小学校,父亲遇到了他人生的几位启蒙老师:我们当地的曹子厚老师,曹玉堂老师,来自河北的赵自耕老师。一个叫马玉卿的老师教音乐,父亲忘记他是哪里人了。其中,赵自耕老师教国文,他功底厚,教法灵活,不拘泥课本,父亲对他印象极深。后来解放军解放南阳,赵自耕老师随军南下,大家才知道他原来是共产党员。
求学的第二年,由于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在此拉锯战,学校停课一年。南阳解放后,父亲在我们村北一里地的楝庄勉勉强强上了二年级。这一年,留给父亲的唯一印象是“学校条件很差,就是一个草房院。”
年秋,父亲重新回到较为正规的常庄小学就读三年级,一直到四年级结束。解放了,国家给适龄儿童提供了更多的上学机会。我们村和父亲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好多都去常庄小学校就读,一时间来来往往,好不热闹。知识改变命运,这一点在这批小伙伴身上得到了证明。(我们村学有所成的有苗文善,苗文兴,苗文之,苗太彬,苗万杰等人)
由于常庄小学校没有高小,再加上生活困难,好多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只读到四年级便不再继续上了。但是爷爷供应父亲读书的决心很大,年秋,父亲到离家二十来里地的太和寨小学读五年级。学校设在旧社会大地主李子炎的非常气派的住宅大院里。班主任姓胡,年轻活泼,是当时少有的女教师。院子的东南方就是当时宏伟高大的大转楼,据说是宛东地区第一座新式楼房,人们俗称“洋楼院”。但当时洋楼院具体做何用途,父亲忘记了。
太和镇李子炎的庄园-转楼后院
小学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年秋,父亲转到离家15里左右的饶良小学校读六年级。转学的原因是饶良小学教学质量传说比太和小学高,学生中有顺口溜:“想学赖,太和寨,想学好,饶良跑”。当时太和寨属于唐河县,饶良街属于泌阳县,父亲的这次跨县转学虽然不要任何手续,但需要自己下点决心。因为其他小伙伴好多还继续在太和寨读书,转到饶良小学后父亲的生疏感还是很强的。看来,择校之事,古来有之。这也说明当时具有一定独立思想的父亲对自己的未来是有一定想法的。因为在当时的农村,高小能完整毕业的人,已经很少了。高小毕业考初中,更艰难了。当时泌阳是一个大县,只有一个初中。但听说准备在父亲他们这一届高小毕业时,要新办泌阳第二初中,所以父亲和同学们学习劲头很大。
父亲小学六年级上学期的通知书(年)至今仍珍藏着
事实证明父亲这次转学好像是对的。饶良小学校当时的校长叫李宗磐,很敬业。当时这里六年级有甲,乙两个班,甲班的班主任叫刑国光,乙班的班主任叫赵庭玺。父亲被分在乙班,赵庭玺老师同时教语文和数学。在六年级秋期期末考试中,父亲在全班33名同学中排名17,属中等水平。虽然赵庭玺老师是第二年教学,并且学历不高——他自己不过是刚刚高小毕业。可他那一年惊天动地般创造了泌阳教育界的一个神话——全班33名同学全部考上,有十几名同学考上泌阳第一初中,父亲和其他20余人考上了新成立的泌阳第二初中。在一起考上泌阳第二初中的同学中,和父亲最要好的是刘清洁和曹绍宗。曹绍宗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乐于助人,颇有古侠遗风。他后来做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直到今天还经常和父亲一起谈天说地,畅谈他们六十多年前的往昔。刘清洁天资聪颖,悟性最高,因为家庭成分高,初中毕业后影响了前程。但是他四十来岁利用一部收音机从零开始自学英语,后来竟然被聘到社旗三高做英语老师。同时他自学中医,在当地行医也小有名气。他的经历成为父亲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经常讲解的励志教材。
其他父亲能记住同学有:有常庄的程广山(教师),仝宝栋,赵岗的田松亮,潭北的王相川(后考入陕西交通大学),饶良街的张西白(医生),陆中峰(医生),三里魏的张运凡(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北王庄的王书芳(女,后任职驻马店地区妇联主席),白鹤里的史玉卿(教师),秦楼的黄留山(北大毕业,后任武钢书记)。
从秋年到年夏,包括战争耽误一年,父亲的小学共经历了七年,先后呆了四个地方。生活的种种困难,动荡局势的影响,颠沛流离的辗转,父亲能够坚持下来并考上初中,实属不易。
(二)艰难困苦的中学
年秋季,父亲15岁,开始了他艰难困苦的中学时代。15岁上初中,今天似乎偏大了些。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属于偏小的年龄。同班同学中比父亲大两三岁的大有人在。当时泌阳第二初级中学的建设正在官庄街热火朝天的进行,于是父亲他们就在官庄街东北几十里外一个叫梅林寺的地方上了一学期多。梅林寺地处深山,山路崎岖,诸多艰难,尽管在此不到一年,可留给父亲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几乎占据了他初中生活的全部。
梅林中学
梅林寺离我们这里百十里地,其中过了官庄街还是几十里山路。第一次去学校大家早早商量好的,近20名饶良小学毕业的同学一起行动。大家先在曹堂村曹绍宗同学家里聚齐,准备由他的父亲护送,因为途中一个叫石门的地方有他父亲的一个朋友,计划在那里中途落落脚。大家早饭后从曹堂村出发,过了中午才到达石门。石门是山脚下一个小村庄,曹绍宗同学父亲的那个朋友,很慷慨豪爽。在那个食品困乏的时代,他支起大锅,让大家饱餐一顿,然后亲自作向导,带领大家去学校。此事留给大家的最深记忆是山里人实在,后来大家又对山里人多了一个评价——“不论理”。原因是有一次去学校在山里问路,第一个人砍柴的说离学校还有10里地。走了好久,问第二个放羊的却说还有15里。大家质问那放羊的,他笑着说其实他们山里人根本就不论里——山高路深,习惯了走远路,不在乎多少里。此事说明山里人生活实在不易。
在父亲记忆里,梅林寺大门朝东,门前有大片竹林,不远一条小溪,风景极好。雨季河水暴涨,常常要快挨着寺门可从没有挨到过寺门,足见古时建筑师的智慧。梅林寺占地约五六十亩,四周围墙因地制宜用片石打底,有一尺多厚,四尺多高,上边再用土坯堆砌二尺来高。这围墙其实防不了盗贼,只为防野兽侵犯。进了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约两三丈高的大土包,土包后有依次两座大殿,一座是教师办公用地,一座闲置。大土包右边一排大瓦房,有20来间,座北朝南,刚好够父亲他们六个班的教室。教室和大门之间有单独小院,里边是教职工宿舍和女生宿舍(当时六个班三百来人,女生不到五分之一)。大土包左侧,座西朝东有几排男生宿舍,宿舍无床,是土坯砌的大通铺。在大土包旁边,有两个简易的篮球场。出了大门东北方向百米左右,有一片塔林,后来学校在塔林旁又修了简易的操场。
总之,一切证明这学校不是刚刚由古寺改建,而是早有办学历史。父亲只记得老师们说一切都是一个叫做韩子步的功劳。我百度了一下,“梅林寺,又叫圆通寺,建于唐或者金,北依虎头山东襟,面临古城之西陲,周围峰峦耸峙,茂林修竹,左右两水环抱,清流激湍,地势绝佳,风景宜人。”年,“政府明令改寺庙为学校,产业充作教育经费。”年,“晁松亭(北大毕业)任私立梅林中学校长,特聘韩子步(清末进士,民国时先后任河南,安徽,陕西省秘书长,河南省水利局长,河南通史馆馆长)任教并管理。”可见,由古寺改建为正规学校,韩子步功不可没。当时学校大门上挂着“梅林中学”的牌匾,正是韩子步的墨宝。解放后,私立梅林中学日渐败落,刚好临时当作泌阳第二中学的办学场地。
学校风景秀丽,历史辉煌都是旁白或者过往。父亲确确实实在这里经受了直到今天我认为都是非常成功的初中教育。除了不学俄语,一切模仿当时完备的苏联教育模式。没有大班额,六个班都是标准的54名学生,直到毕业,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这一点就让今天我们的学校汗颜。那时没有主副科目之分,除了语文,算术,几何,代数,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卫生常识,地理,历史,其他即使音乐,美术,体育不及格都是要下期补考的。每周有三节体育,两节音乐,两节美术。因为吃不饱,同学们体质差体育课老师要求不是很严厉,其他要求颇高。比如,美术最终要会素描和写生,音乐则最终要学会开谱。每天早上一节课,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另有一个半小时的课外活动,活动内容有体音美,说唱,劳动。晚上一节课,照明用汽灯,煤油灯(灯油费每学期5毛)。令人惊讶的是,从来没有课外作业和假期家庭作业。现在流行素质教育,可作为一名中学教师,我一直对现在的素质教育不敢苟同。六十多年过去了,素质教育在专家教授们的指导下,终于让中国城乡的孩子们都过上了炼狱般的学习生活。
父亲当年使用的教科书
那时候全国一盘棋,城市支援农村。学校校长叫庞安国,泌阳本地人。教导主任叫任舒广,南方人。三年中老师基本固定,所以和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父亲的班主任叫贾培如,陕西人,教算术和几何,对学生关怀备至。语文老师叫赵罕,北京人,古文功底非常好。物理老师叫李晚成,安徽人,是国立河南大学大学的高材生。其他教师也大都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个个修养极高,满腹经纶。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他们舍小家,顾大家,抛妻舍子,不远万里从各大城市来到偏僻的深山古寺,为我们当时贫穷落后的家乡,播下了文化的种子。父亲和同学们沐浴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学习兴趣极高。
和精神上的极大满足感不同,物质上的匮乏给学习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时同学们户口都转到了学校,国家每个月每人划拨30斤粮食,主要是豌豆面和少量白面。另外每个月大家额外交给大伙三五元不等的伙食费。约一半家庭困难的同学有助学金,从每月两元到六元不等。早晚主食是豌豆面馒头,经常蘸着红辣椒吃,喝蒸馒头笼屉下边的蒸糖水。课余,同学们经常去山里挖各种野菜交到伙房,以弥补菜食的不足。中午偶尔喝白面做的素面条,是大家最兴奋的时候,好多同学端着碗去大土包上边喝,场面甚是壮观。年元旦,大雪封山,官庄街物资运不上来,大家足足饿了两天。国家困难,这样的伙食让正在长身体的同学们苦不堪言。体育老师做了实验,让全班同学蹲下几分钟,一半以上的人站立起来都非常艰难。
和单调匮乏的饮食相比,每月一次的家校步行往返更是让父亲刻骨铭心。一百多里地,途径大小13条河流,均无桥梁。在当时全靠步行的时代,每一次往返都无疑是一次悲壮的远征。第一次回家大家没有经验,周六下午上了一节课才离校。由于在山里迷路,天快黑了才走到官庄街的平原地带,到家里已经是半夜。在家里呆了几个小时,周日早饭后再次出发,赶在天黑前回到学校,每个人的双脚都磨了好多泡。年元旦那次,尽管周五早上请了假,早早出发,但是连日大雪,山路难行,真可谓“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走了不多久棉鞋和棉裤已经湿透并结了一层冰。过河时脱鞋,挽起棉裤已经失去意义。有的连小便也洒在棉裤里,仅仅为了冰冷的棉裤有一丝热气。可见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人的自尊根本无法顾及。一群人傍晚才走到郭集街的古城寨,找了个简易饭铺吃饭。饭铺主人好心肠,看到这一大群少年实在悲惨,难民一般。于是弄了一大堆火让大家先把衣服勉强烤干,然后,每个人两毛钱,牛肉汤管了个够。半夜回到家洗脚时,鞋子和鞋带都结了厚厚的冰,根本脱不下来,活活变成了一个铁榔头。
每次返校进山,大家都必须在山脚下聚齐再走,以防意外。最惊险的一次,是进山的路上,在黄昏的孤庙岭,父亲和这帮同学竟然遭遇了五六只狼组成的狼群。由于冬季饥饿,它们在不远处尖声嚎叫,双方对峙了半个小时左右,狼见同学们人多才悻悻离去。这期间,队伍中仅有的两名女生早已吓瘫在地。那是父亲最心有余悸的一次,“其实,每次天黑了走山路都能听到狼叫,独狼并不要紧,它们也怕人。”父亲补充说。
年春季的下半学期,官庄街的泌阳第二初级中学建成,学校搬迁到官庄街。学校离家近了四十里,并且没有了山路,往返容易了许多,其他方面比如匮乏的伙食依旧。毕业前夕,由于泌阳第一初级中学办了高中班,更名为泌阳高级中学,父亲所在的第二中学便更名为泌阳第一初级中学。所以父亲在泌阳第二初中上了三年学,得到了泌阳第一初级中学的毕业证。
泌阳第二初级中学年父亲的通知书
初中三年的成绩
父亲的初中毕业证书
年春季父亲面临初中毕业,那年3月5日刘少奇在许昌中等学校发表“许昌讲话”,号召同学们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那一届学生三百余人,只有六人考入师范,十几人考入高中。(那年唐河,泌阳,桐柏三县高中共招生两个班,余人)。父亲和其他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回家做了农民。
(三)造化弄人的中专
年毛主席发表了“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讲话,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在此背景下,当年豫剧《朝阳沟》风靡全国。父亲响应号召,在家里继续生产劳动,准备在农村大干一场。但是同年夏,唐河县速成师范班开始招生,在我们乡,父亲唯一一个考中。
速成班学制仅半年,当时政治空气已经非常紧张。在第5个月左右,父亲和其他几十名同学因为“胡乱说话”被学校除名,并且因此戴了好多年“右派”的帽子。至于“胡乱说话”的所指,在今天基本就是党内整顿纪律作风的绝好典型——在那个同学们经常为每天三四毛钱的伙食费犯难的年代,一个月工资41元的后勤副校长却每天一包一块八的香烟。在一次班级民主生活会上,幼稚的父亲竟然对副校长的生活奢侈提出了批评。在那个乱扣帽子的时代,父亲最终没有拿到速成班的毕业证。后来我仔细研究了父亲珍藏的几份他初中时期学期通知书,评语一栏大都有班主任贾培如老师“性格直爽,但脾气急躁”的警示语。感觉性格决定命运,一切似乎冥冥中自有定数。但是很快,毛主席发表讲话,“对全国学生整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一风吹”,父亲虽然学业被中止,但是由于当时身份是学生,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伤害。
年冬,饶良街的一个亲戚从青铜峡给父亲来信,说他正在青铜峡平整坝底,听说国家正筹建青铜峡水利学校,希望父亲去报考。父亲冒着当“流窜犯”的风险,带着家里东拼西凑的二十多块钱,偷偷步行三百余里先到许昌,再坐火车前往兰州,参加招生考试。这些钱只够去时的路费和饭费,可以想象父亲一路上破釜沉舟的种种豪迈和背水一战的诸多无奈。在兰州,父亲获得了第六名的好成绩,于是兴高采烈的去青铜峡水利学校报道学习。
青铜峡拦河大坝
青铜峡水库
学校一切按照苏联老大哥的规划设计,父亲他们作为第一届新生,共有12个班,余名学生。学校的服务对象是在建的青铜峡水利枢纽,长远为三峡工程做准备。同学们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大坝前期的各项生产劳动。然而好景不长,几个月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撤走大批援华专家,包括该校众多专业老师。于是,学校解散,苏联老师和中国学生依依惜别,相拥而泣。这一次让父亲深深感受到:浓厚的师生情在国家大势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年底,父亲重新回到家乡,继续做农民。
父亲在柳树庄小学任校长时期留影
年到年,父亲一边做农民,兼做生产队的副队长。生产队有余人,耕地余亩。父亲对集体倾注了太多心血。田间地头的所有沟沟坎坎,生产队的骡马牛羊,父亲到今天都如数家珍。年,作为当年唐河师范速成班学生整风事件的受害者,父亲第一次被平反,在苗店乡石塔寺初中教了9个月的语文。但是这次平反并不彻底,做老师还不到一年,上边让父亲继续回家种地。年,父亲第二次被平反,先后在苗店乡教办室,赵岗小学,柳树庄小学,苗店乡成人教育学校工作。年,父亲光荣退休。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退休后的父亲带孙子孙女在唐河革命纪念馆前留影
父亲很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
后记
生活和工作中,我无论遇到多大的烦心事,八十岁的父亲都会乐观的用“没事儿”“怕啥”来安慰我。我一直认为他只是天生疏旷,心大而已。今天,我一边听父亲详细口述自己的求学经历,一边整理。我由衷的感到:人的心胸,真的都是撑大的。所有的苦和难的经历,冤和屈的洗礼,只能是使人坚毅如山的熔炉和催化剂。而那些曾经把人打的遍体鳞伤痛不欲生的往事,最终都会变成风中零落的些许鸡毛和蒜皮。
年8月苗松克
作者简介:苗松克,苗店中学物理教师,社旗县苗店镇大苗庄人。喜欢读书往往不求甚解,爱好写作常常辞不达意,自认为涉猎虽广,无一精通。向往无拘无束,恬淡悠然的人生。
苗松克文章导读:
1、北山行
2、马河的忧伤
3、致我们随风飘逝的青春(上)---献给年毕业的师范生
4、致我们随风飘逝的青春(下)---献给年毕业的师范生
编者的话: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松克老弟这篇回忆父亲的求学之路终于出炉,松克的父亲玉端伯是我父亲多年的好朋友,我父亲年在苗店担任棉花种植技术员,就吃住在玉端伯家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们两家一直在走动。
年6月我们一家去大苗庄看望老人,伯伯、大娘和母亲三位老人在叙旧。
没有松克老弟的文章介绍,真不知道玉端伯当年的求学之路这么曲折,这么艰难。玉端伯平反后一直在基层从事教育工作,如今光荣退休在家,在院子里养花种菜、颐养天年。在此祝愿伯伯和大娘两位老人健康长寿,天天开心!
-----赵华胜
欢迎点击文章标题下方的蓝字“赊旗兴隆镇”或者再下方长按识别
转载请注明:http://www.wuzeia.com/yymj/92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