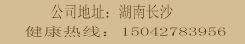![]() 当前位置: 乌贼 > 乌贼的天敌 > 谈谈小疼长篇小说乌贼的探险性阿坚
当前位置: 乌贼 > 乌贼的天敌 > 谈谈小疼长篇小说乌贼的探险性阿坚

![]() 当前位置: 乌贼 > 乌贼的天敌 > 谈谈小疼长篇小说乌贼的探险性阿坚
当前位置: 乌贼 > 乌贼的天敌 > 谈谈小疼长篇小说乌贼的探险性阿坚
在性文学领域,《乌贼》是一部探险般的长篇小说。探险,有可能失败、完蛋、千人所指,有可能开拓新的可能、新的合理,甚至新的法。有的探险之僻径,终将成为鲁迅所说的“走的人多了”的“路”。有的路,将被证明是死路一条,所以在将来之前,探险者是要做好牺牲准备的。
我不是很了解作者小疼。不管《乌贼》有没有、有多少纪实的成份,我只把它当作小说对待。甚至我认为,文字的探险有时比身体的探险更有残酷性、高危性。哈姆莱特的话应该改成:是疯掉还是死掉,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对文字探险的小疼表示关切。
一般读者可能会认为《乌贼》的作者是豁出去了,比拼了命还要更少见的“拼了性”了。我却觉得,我不知道是否拼了。有人天性不安生、要折腾,受不了庸常,要超俗,这种人的本能就是要探险。还有一种人,本能里潜藏着探险的因素,一旦机缘出现,就被探险主导,如果从不邂逅机缘,其探险本能虽生如死。探险的本能,是说可能性;本能的探险,是说既然性。我不擅定义,总之,后者是以探险为生。《乌贼》,我把它归为后者。也即是说:在作者的文字里,探险就像玩一样,高兴,来劲,危险是高兴的助剂,逾矩是自然的法则。有人问登山探险家植村挑战与生命的问题时,植村回答:我不挑战就没有活的意义。植村死于山难,他创造的亚洲人无氧登山记录,引领着后继者。
2、性如老虎,偏摸它的屁股,偏骑着它玩
武松也本事有限,他只会打死老虎,他无能力骑着老虎玩,把虎驯成他的胯下。性事或性写作,有些像老虎,它有着夺人的魅力,也有着伤人的威力,它让一般人不敢过于沉浸,它让一般作者不敢过于放纵,所以才有谈性色变之说。小和尚下山遇到的女人被定义为老虎。
读《乌贼》,这小说有偏向虎山行之勇气、之霸气,并不乏顽皮,不光摸老虎的屁股,还骑着老虎玩;我为作者捏着一把汗的时候,骑虎者已经高兴得出汗了。这么谈性,这么玩性,性受得了么。我听过一个后现代版武松打虎:景阳岗上的那是一只母虎,武松一手撅着老虎尾巴,一手用哨棒捅虎的阴户,开始那虎还舒服地哼哼,后来哨棒都捅断了,虎受不了了,说:松哥,你还是打死我得了。
我是想说:作者写性太厉害了,不是如椽大笔,而是如松哥哨棒之笔。我读《乌贼》时,多次掩卷,就算是被就惊着了,就算是被累着了。
好几年前直到今天,我一直敬佩一位做爱写爱的女英雄木子小姐。约六七年前我就写过一文,大意为:颓废探险者北有狗子,性爱探险者南有木子,他俩都在自由的边缘地带拓进,是开路先锋。尤其木子小姐让我惊赞:狗子是喝得牛逼,木子是活得牛逼,简直是长着牛逼。
我觉《乌贼》的文字性与木子小姐的实践性,在孔孟笼罩两千年的中国,都有以身试法(则)、以身破法,以身立法的破处之效。她俩不是一般的女人,否则早病了、早疯了、早被唾液淹死了。至于她俩革命性的效果,是不是有趋众性、一般性、进步性,我们还得容忍时间来统计,但其出发点是就于基本的人性。她俩也会原谅伦理的发展总是慢于现实。
3、“存在先于本质”,先写存在,本质再说
《乌贼》写的是存在:已婚育子的中学老师郭娟,爱上了丈夫的高位截瘫的朋友季宇斌,开始了不择手段如装跳楼、装癌症式的追求;郭对季爱的基点和兴奋点乃至幸福感是残疾者的尴尬痛苦、无奈绝望;爱之甚而无所顾忌,不在乎离婚、学业、工作等种种市俗,性之甚也无所顾忌,一切姿式、方式甚至吃屎都可为至高的性情所用;彻底披露了健康女性与畸形男性间的性之可能、欢乐之可能;尤其表现出人的愉悦、“嗨点”可以来自非高尚、非美观者。
虽然小说中有不少议论、评判甚至引用一些哲学大师的观念,但那些都是可有可无的疑似本质,我把《乌贼》看成是一部存在式的小说,也就是说它是写事的小说,以叙为大观,以实为异景。
存在是不是合理的,这是哲学家关心的研究的,我只关心存在,因为大千世界有这样的事、这样的人、这样的关系。丰富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丰富的可能。恶的存在,善的存在,已多有典型和类型。恶与善之间的领域,也许比单纯的恶单纯的善宽广多了,它们划分了很多的区域,细究起来,可以像纬度那样化分;南极和北极只是两个点,是绝对标点,而看看地球,99%以上都不在极点。
《乌贼》写的是存在中的一个纬度。这个纬度人事密度不高,披露不足,但却是一个重要的纬度——随着社会的残疾人越来越多,也随着性话题越来越常识化。有年青人慕名翻了金瓶梅后,说:尽骗人,它哪是黄书?
我虽是基本健康、正常的人,也没对畸型者有特殊的性感觉,尽管朋友们说我是“色鬼”、“思想淫秽”,但都是常识般的评判,庸俗窠臼之论。我仍然觉得:因为阅读《乌贼》,其畸形的存在不是一点不能辐射到不畸形的存在;畸形与非畸形没有一道明显的界线;古代的不少“畸形”“虐形”到现代已经正常,不稀罕了;性可以像一个肉洞那么浅,“捅咕”;也可像一个黑洞那么深,“通古”。
4、“能说的说透,不能说的闭嘴”,维大师这话错矣对矣
一般存在是,能说的也说不透,不能说的该说还说。你已为你能说透但你透的标准太低,你以为你闭嘴了可你的眼色、举止比说话还张扬呢。看得出作者对存在哲学的迷恋,也看出对“能说”与“不能说”的质疑。
我没有作者小疼的大无畏精神和思想裸奔的力量。比如我就像个民国时常逛八大胡同的文人(据说胡适,郁达夫都不吝),我的思想到行为再到文章,是预留了几个档次的,一档压着一档,关于性:有的可想不可做;有的可做不可说;有的可说不可写;有的可写不可播。这每一档,都是一个递进,或说,每次退一步(档)都是为了保卫身后的那个机密——我的阵地像洋葱皮一样一层一层失去,天那,我快没有退路了。
常有人恭维我是老流氓,让我教教如何行事,我也只能凑一首诗做答: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水中自然直,两岸猿声啼不住,一只红杏带雨湿。
想而不说,说而不做,做而不写,写而不播,为什么呢?其实我也在琢磨,弄不透,是禁忌还是敬畏?是谦虚还是低调?是虚伪还是自律?上面的四“而不”,第一“而不”俗人想不了太丰富,第二“而不”便于吹牛逼,第三“而不”闷得儿密,第四“而不”为藏诸名山,这四“而不”后面可能有大东西,《乌贼》的作者可能看透了无所谓了无所不谓了,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这样的可能,就是作者傻呗,哪怕那傻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之傻。可能我评《乌贼》就是愚者之见。
5、性瘾与毒瘾
《乌贼》中男女主人公的性爱,从渴望到成事儿,从摸索方式到熟练再到花样,从常态到异态,然后,双双上瘾了,似乎也看到了瘾之尽头是什么,比如“酒瓶破头”出现了,比如“以枪抵头”出现了,双方不止一次有戒意,但自然的力量——瘾也是自然,是强大的。几乎如同上了毒瘾。男主人季宇斌像巴甫洛夫实验笼中的小白鼠,已离不开那快感的触板儿,本来他可是与快感绝缘的人,虽生犹死也几次欲绝,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关键是林妹妹把他这个废人当成贾宝玉,这种洪福太摧残人神经了,并且是自比丫头、性奴的郭娟把他改造成了牛逼的人,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这个毒中的太深了。女主人郭娟这个性冷症者,唯那一位残疾者的病态、异举能给她满足——她忽然发现这一片幸福大陆后当然得全力奔赴,这是一片罂粟花美丽而深刻的大陆;本能趋使,义无所顾。“吃过咸的人,怎能再离开海”。卧操,世界上还有这等爽事。
确实,《乌贼》中的性之床像烟之榻,性之爱像毒之美。
当然,上瘾的结果是可怕的,曾经沧海难为水,天仙配后岂能俗。作者可能也不敢往下写了,当双方互戒了一段时间后,终于都坚持不住了,一个电话,郭娟又去找季宇斌了。所以,这就小说没写结尾,它应是可怕如火的,或是沉寂如冰的。性的尽头与毒的尽头应是死亡抑或轮回,作者止步了,也饶了我这样的观毒者。知道作者是个三十几的女性,便谅解她把悬念留给时间,她毕竟不是“我吞噬死亡就像呼吸”的普拉斯——是拿生命写作的人,比身体写作要高端的多。如同以毒写作比以性写作要高端的多。所以《乌贼》没写完,就算不可说的就别说到底吧。性能伤人,毒能杀人,写瘾之笔也是能把自己带往极端之境的。我想起朋友王爷评论《尚书》的魅力就是不写极端,只写极端的周围。
6、“硌硬”是存在,怎么写
三级片当然是讲美感的,得让人看着顺、看着自然。脓疮、垃圾等是丑的,是反自然的。也就是说,存在的东西不见得是自然的。《乌贼》中有不少对性器的状物写法是让人不习惯的,不自然;对一些癖好的叙述也是欠斟酌的——“硌硬”是存在,怎么写“硌硬”属于高级的文字能力,此点恕我无力论述。不用说庄子,就是兰陵笑笑生对于描写“恶心”都极为慎重。我读《何典》,有关性器的细节,我觉写的逼真而不觉“硌硬”,反觉传神。我读《不二》的交媾情节,绝无低档俗烂之意,而是充斥自然之法。应了一个老嫖客的说法:小逼通大千。
写性是门高超的手艺,甚至是“思艺”或“诗艺”。我看见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的破竹如泻之力,反羁拌、反装逼,一览无余。甚至我有一种感觉:作者把读者从阔小姐改造成了婊子,把有洁癖的名媛玩成了无所谓卫生只要快乐的荡妇。身在其中,这仿佛是一切革命,但却留下“硌硬”的阴影。存在太粗砺了吧。
阴户和面容,哪个重要,这好像是个哲学问题。看到一个宜人面容,好色者在想什么。仅仅看到一个阴户,好色者多半迫切地想往上看到面容。当然在阴户和面容之外,还有重要的整体或性情的感觉——这是诗意的存在。《乌贼》中对各种诗意有着极“湿意”淋漓的笔述,只是这种比重比《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要少多了。
我想起黄仁宇文中引的一首湖南民歌:太阳一出满天霞,思想小冤家,想起冤家遍身麻,昔日来调情,一切说得真,说得水里可点灯。
这一节我是想说,“硌硬”或“恶心”不是不能披露,关键要看有无平衡它们的诗意或说魅力的存在。俗说:不怕逼丑,就怕人丑。
7、邪恶比善美更有力量邪恶比善美更有力量,《乌贼》做了些证明,颇有新伦理学的意义。先说邪或斜,其反义是正。女主人公郭娟对季宇斌,审丑为美,一反一般人的高大、健康、干净的标准。比如爱人瘫着、趴着比矫健的步姿要性感多了,爱人因不常洗澡而积出污垢是不脏的可以入嘴的,爱人因烦或疼的言语或声音是动听甚至是能令人起性的。刨去女主人公部分审美的个性,其癖好也不能说没有一般性,只不过囿于常识而不被别人抖落罢了。所以这一点看出作者小疼的魄力。
干嘛要符合大众美学,我这么舒服我就这么做,我这么来劲我就这么做,关键是这么做没有伤害谁——它不是恶,只是不“雅”。其实性情激荡的恋人都有不“雅”、无忌的举止。所以读到《乌贼》的不少性爱片断,真让人想起狄伦·托马斯的诗:“让一切去见鬼吧,除了表达的必要和表达的媒介,除了为神秘本身以及我呻吟的意义,……只有一个目标,除掉你灵魂的面纱和你身上的血痂。”
斜或邪只是不正统不传统,但没有造成伤害;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要明白别人的痛苦是先有的,而自己的快东是后建立的(如果我已痛苦了,又能博得大家一乐,我这痛苦似乎也值了)。我想强调,《乌贼》中除了别人管不着的斜或邪,它还有一种恶的力量,比善更有强度。比如郭娟几次故意制造季宇斌的痛苦:医院抢救,第二次拍发假跳楼现场彩信,第三次以同事名义电话通知已跳楼。这种手段真是有些恶,效果良好,因为季的痛苦极痛,而促进了郭的高兴极高、湿意纵横。读到这些情节,我有点冒冷汗。作者不吝宣露恶之花,魔力四射,我却无比同情可怜的瘫子季。我中了作者之计了,“恶人计”比美人计更有力量。读恶的东西,人会兴奋,我也不善。为什么没有“善作剧”,只有恶作剧,因为恶更易有戏剧效果,因为恶是人身上的存在之一。和平下的残忍,诲邪诲恶,不知小疼是什么材料做的,身心是什么结构。
8、《乌贼》有社会心理学的一些重要信息
比如郭娟在失恋(严格来讲叫“不得恋”)状态,爱吃贪吃,为了不断有食道的快感,便自我催吐——吐的瞬间也是舒服的。这种心理又导致生理的行为,弗洛伊德好像没总结过。说白了就是,阴道不足,食道来补。
比如粪坑捞书的情节,郭娟不嫌其味,不仅有敝帚自珍的意思,重要的是这里有一种心理学上的“情境如照”的关系。即郭娟不怕名声臭、臭不可闻;名著沾过粪坑,名著依然是名著,——怎么着,我就当沾过万人屎尿的名著。
《乌贼》中大量俚语或曰“脏词儿”的运用,真接还原了日常中“原声态”——这非常重要。脏活在底层人中太正常了——不脏不会说话,有的口头语就像发语词或韩语尾句必带的“司妈逮”。就算绅士淑女们不用脏词,那也只是嘴上,实际上想“操”,但心里的语言会是“用阳具进入对方阴户”么。所以有关性事的心理语言,君子与小人差不多吧,当然在心理画面(即配图)上,君子的是整体,而小人的可能只是关健的局部;或者小人是见山见山,君子是见字如面。
屎脏么?爱人的屎脏么?令人想疯了的爱人的屎脏么?《乌贼》里最极致的性情描写即为高兴(绝无为辨病、打赌等实际意义)而食爱人的屎。女主人并没疯,很正常,像玩一样吃的。这也许不算为心理学提供案例。不过,很多可吃不可吃的标准来自心理;比屎难吃的东西只要有意义也可吃。我想信,林黛玉的尿会有人抢着当美酒的。
总之,我觉社会心理学家能从《乌贼》中找出大量细节来比对一些学术观点,尤其在性心理学方面,它算小百科全书吧。
9、20年后看《乌贼》的性写作可能是很正常的
忘了谁说的,“相爱如通电,我非点亮你”。《乌贼》的故事,是电一般的故事,低压电、闪电、高压电,就差电死算了(前节已述过这是无尾或不敢有尾的小说)。郭算一个有高知文凭的超现代女性,而季至多只是平庸的小公务员,这不妨碍二者的通电;民间讲话叫“对了眼儿了”。读到有的片断,我像看高级(丰富、深刻)的毛片儿,激动之余,我还与也瘫痪在床的音乐家梁和平聊其目前的性况。多年前就有老炮跟我讲过:跟老婆,越简单的操越好,别玩花活,别让她上瘾,否则你会受不了的。
作者小疼写得过瘾,但也许我太老(就算老流氓也是老派的流氓),难免觉得这样写是不是太超前了。几个月前我评诗人小无的充斥逼与操字眼儿的诗集时就说过:遮羞布的深刻力量在于让性有更丰富的形而上、性而上的魅力;现代社会了,词语的裤衩不是不可以脱掉了,有人先脱、先亮出来,无可厚非,但要容忍性风俗滞后的惰性;也许20年后,直接无忌的写作属于通常,所以我理解你们是先锋了20年。
读小疼或小无的性作,我当然觉有些硬有些大有些直,我有时更喜欢读稍软稍弯者,如保罗·策兰的,“……我们口说真理。我的目光落到爱人的性器上,我们互相看,我们交换黑暗的词语,我们相爱像罂粟和回忆……”。估小疼和小无会觉这写得装逼,但我有时以为“河豚要吃鳞,操人要操心”,还是策兰更能运作到人的心里。
10、《乌贼》可贵在于年青生猛,可指责的并不重要
那我也瞎责一通如下:
总体过长,30万字可删去10万;
前戏过长——即郭、季相好之前写的稍多不紧凑,最好不要玩《霍乱时期的爱情》那种铺张;读者的时间也是宝贵的;
关于“学佛”、“尼姑”与性的那种写法,非常重要,但这涉及过深、倒应“舍得一身剐”地多展开;学学冯唐的《不二》或王朔的《我的千岁寒》。我不知小疼的涉佛历史与能力,但这是必须的,就如同反佛教的胡适对佛研究很深,简直揭开禅宗史的伪造;
有的三级片真好,是文化,是哲学,但有的无性的电视剧等,写的脏、演的猥琐下流。作者的阅历也许有限;
不少乡村学校场景、山村乡人、小城景物,写的好,但不如《金瓶梅》写的是历史画卷;要为历史写作,焦点为性,焦距广阔才更翔实;有时需要为读者推开卧室之窗,看看山野乡俗;
《妓女史》不是妓女写出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工作;虽然作者学历很高,我觉知识储存(有关残疾人心理、性理及恋残社会学)还不够;甚至我以为要写瘫子,也应研究瞎子和聋子;
最后一点,小说基本是流水账,为何不玩结构——当然乱炖也是好的。昆德拉若是有《乌贼》的素材,乔伊斯若有,那就不是此《乌贼》了,当然,结构是后现代风格中较难的精神劳动,我们不好意思强求作者。反正读罢,我有些心疼,不见得是心疼作者小疼。
(感谢贾新栩为我复印30万字的《乌贼》,感谢高星、孙民、张弛为我提供的见解,感谢西局书局为此文打字)
.4.13
阿坚感谢
转载请注明:http://www.wuzeia.com/yyjt/8807.html